对话 | 渠岩、向丽:从艺术到乡建,一种先锋性实践
当代艺术的内核是观念的表达,它内在地包含着“现实的批判性”与“文化的针对性”,实则是要表达在社会转型和变迁中人生存的状态和尊严,其核心价值正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表征与重构。在此意义上,艺术乡建就是一种当代艺术实践,其先锋性在于将艺术与社会生活重新联结起来,并成为社会生活关系重构的某种预演。在城乡艺术建设中,形式主义美学是思想的末端,在此意义上,艺术乡建是一场“去艺术化”的革命,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触动文化本身。乡村是由天地人神共同构成的文明系统,艺术乡建正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找回那些走失的神性和人性,在城乡之间形成持续性的、交互性的彼此馈赠,从而真正践行关系美学的路径,并最终在脉搏相连与同频共振中通达城乡互愈。
向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审美人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渠老师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腾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们分享您和团队近20年来的艺术乡建实践与思考。我和云南大学文学院审美人类学团队深感荣幸,能够在昨天(2024年5月31日)见证“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高校艺术乡建教学联盟”揭牌仪式。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的成立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艺术乡建,意义非凡。一方面,中国艺术乡建实践已走过了20余年,研究院的成立提供了关于中国艺术乡建回顾、对话、展望的平台,比如在昨天的“艺术乡建:时代变革中的乡村复兴”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以其多年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思考,呈现了关于“可持续”“赋能”“社会学转向”“破局之道”“原真性”“自主”“乡村美育”“乡村创意”“文脉传承”“居间经验”“城乡实践”“公共艺术”“日常生活艺术实践”“在地实践”“边缘地带”“行动戏剧”“新乡土”“非介入的介入”等乡建理念与实践之道,表达了对于当代乡村新的感知与经验,以及在中国乡村遭遇百年损蚀冲洗之后如何从其残损中衍生出新生的多重“身体”的重构旨趣与愿景。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这样持续的交流与对话,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可以为后续的艺术乡建以及城乡互动,乃至全球文化生态平衡重构提供持续而坚定的行动指南。
此外,我还想表达与您相遇的缘分,这样的缘分在我看来主要源于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乡建的某种契合与多向共鸣,如杰里米·库特(Jeremy Coote)和安索尼·谢尔顿(Anthony Shelton)所言:“审美人类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考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如何‘看’世界。”这种“看”世界的方式也正是人对于世界与社会的审美经验及其重构。不仅如此,审美人类学还有一种基于边缘反思中心的缺失的批判精神,在“让”小写的复数的“美”得以如其所是显现的基础上,发掘和阐释审美与艺术的能动性以及美的创生机制。概而言之,审美人类学接衍着美学的当代转向,积极探讨美学介入社会的机制与力量,并充分肯定艺术行动成为介入社会转型与变迁的曲折而微妙的当代性策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乡建之间形成了深度的契合。您是“中国艺术乡建新浪潮”最早的发起人与实践者之一,也是长期活跃于国际与本土的当代艺术代表人物,您对于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念的持存以及艺术乡建的本土践行,让我们心生敬佩与感动。以下我们将主要就您从事艺术乡建的历程、城乡互动与共生、艺术乡建的未来等问题向您请教,并与您交流。

“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高校艺术乡建教学联盟”在广州美院正式揭牌,同时举办“艺术乡建:时代变革中的乡村复兴”学术研讨会,2024年5月31日,图片由向丽提供
向丽:您昨天在会议中回答“服务器艺术”“打边炉”“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媒体的问题时谈到,不同的人介入艺术乡建有不同的背景与经验。您是如何经由对当代艺术的经验转向中国艺术乡建实践的?又是如何通过近20年的艺术乡建的在地性实践,重新理解和创造当代艺术的?
渠岩(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非常感谢向老师及团队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见证广美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在华南地区的升级,并给予我们支持。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本身包含着“城乡”二字,这是有意味的,部分学者可以敏锐地感知到,正是在城乡互动与共生关系中才能同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这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我不同意“城市反哺乡村”的说法,因为历史上城乡有各自的文化价值,二者之间的脉搏始终相连与共振。从我个人的经历、创作的转型、实践与教学和研究来看,我的确经历了从艺术创作到乡村建设的转变。而从艺术到乡建,表面上看蕴藉着空间的变化、方法论的转型,这似乎是一个大的跨越,但在我看来,它们在艺术表达上是一致的,首先是在面对文化问题和社会思考上是同步的,只是方法、语境、空间、环境和表达与表现上存在变化和差异。
我们始终坚守当代艺术自身的文化思考与时代要求。国际上最重要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两本著作,均收录了我的艺术乡建实践和作品,它们首先肯定了我做的事属于当代艺术范畴的创作实践,而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当代艺术的内核是观念的表达,它内在地包含着两个关键词:“现实的批判性”与“文化的针对性”。而事实上,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否真正触动文化,唯如此才能真正构成艺术的拓展。
近年艺术界常提及,西方是以观念的嬗变来推进艺术史,而我们中国艺术则靠技法的延续来书写美术史。艺术家所思所为其实是需要超越这种书写方式的。艺术家也不能依靠和仰仗世俗的成败来判断其价值,在此意义上,艺术家必须永远失败,因为与其相对应的成功往往是所谓现实层面的,有些实践在当下可能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也可能会在现实中遇到了困难或者遭遇失败,而艺术家往往用自己的失败来证明自己的胜利,所以不必关注结果。
这同样在回答以上您提到的问题。我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介入乡村、用艺术家审视的眼光看待现实的,这与学者以及设计师们有着本质的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截然不同,所以我说“身份决定态度”。而我的身份主要基于在20世纪80年代做前卫/先锋艺术所同构的身份。就是所持有的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以及对现实永远抱有的抵抗意识。现在很多人仍然在怀念这个时期,认为它是曾经的最好的时代,甚至把它与南宋、五四时期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实则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中国了解到西方的一些观念。我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时代,艺术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服务功能。比如,延安的木刻、行军时的快板编唱等服务于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和救亡图存,展现出了革命美学的意义和无序蔓延后的某种狂热与盲从。“85美术新潮”所酝酿的审美意识形态不满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单一政治功能的价值观,当时的艺术家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养料。1989年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喧嚣褪去,中国先锋艺术陷入沉寂,先锋派艺术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和空间,艺术家作鸟兽散并纷纷出走。20世纪90年代,我绕道去了东欧,到了刚刚解冻后的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是二战以前欧洲的汉学中心,布拉格是汉学研究的重阵,比如查理大学有汉学系,布拉格也有东方研究所,对于东方文化和艺术的研究比较成熟,我正好在美院找了一个教授书法的工作。书法本身不是语言学而是艺术学。他们也把书法纳入西方抽象艺术的系统中加以认知,并在此过程中去体验中国“气”这一审美范畴,而非仅仅局囿于文字语义本身。当时东欧正值时代转型,东欧知识分子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当代艺术方面。艺术分两个阶段,以西方艺术史来区分,比如古典艺术强调再现美。在照相术发明之前,艺术代替照相机去再现风景,或是表达和服务于宗教。二战以后,现代艺术诸如毕加索、达利的作品主要是要创造审美。到了当代艺术,就无法按照某些既定的美学原则和标准进行评判了。而且,当代艺术的旨趣根本不在于美学形式,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危机(诸如战争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当代艺术实则是要表达在社会转型和变迁中人生存的状态和尊严,其核心价值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表征与重构。你如果从这个线索来梳理,那么艺术乡建是不是当代艺术就不言而喻了。因为乡村危机带来了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在审美判断之外,更重要的实则是伦理判断,它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观在乡村建设中的乡建伦理问题,这是我在艺术乡建中较早提出来的问题。
在捷克的生活让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让我更加坚定地意识到,艺术家首先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此外,捷克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是诗人和学哲学的,而我们那一代人在艺术创作学习中往往讲求技艺和修炼技法层面,一旦离开了客观描述,我们真的一无所知。西方知识分子往往以观念为先,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写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他强调要独立批判既定的秩序,这一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内心里都有中国士人的情结,比如有修齐治平的心态秩序与自我要求,在这一点上其实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契合之处。再比如,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社会雕塑”,就是以艺术行动唤起社会民众精神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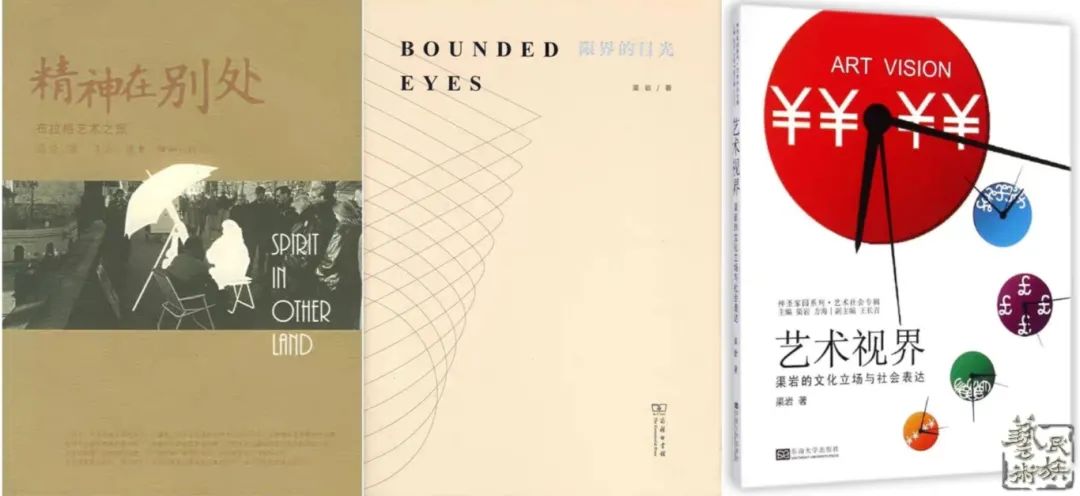
渠岩的部分著作。图片源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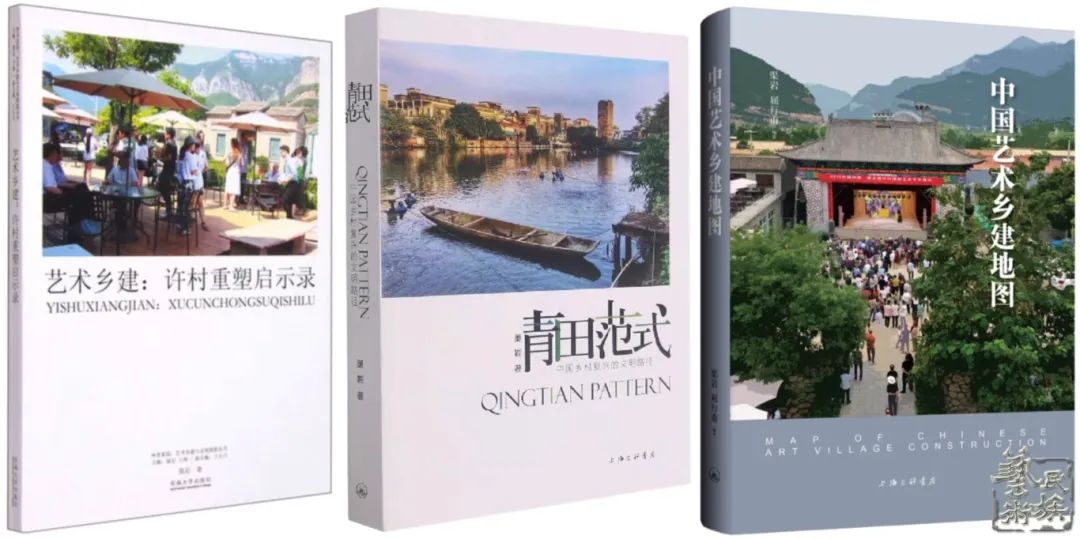
渠岩的部分著作。图片源自网络
向丽:您在“85美术新潮”运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在布拉格的艺术经验,对于您如何理解与坚持当代艺术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您又投身于艺术乡建实践之中,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于物像艺术的超越,通过行为艺术最终转向了行动艺术,亦即从观念的变革层面重构对于乡村的感知与参与建设。
渠岩:艺术如果不触动文化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很多人既不理解也无法表达出来。审美其实是思想的最末端,它更多的只是一种视觉表达,我甚至说了一句更重的话,我说:“审美只是思想的排泄物。”
向丽:这的确是一种让人惊颤的表达,但我想,您其实想表达的应是要超越西方传统的形式主义美学。
渠岩:是的,我并非要否定审美。我是说审美必须建立在观念之上,没有价值观在先的审美,最后都变成了视觉游戏,以及作为审美为先和唯一手段的乡村美容术与化妆术。
向丽:在美学的当代转向和审美人类学视阈中,“审美”实则是指人的审美经验的重构,它恰恰正是作为一种观念持续地灌注到艺术创作理念的嬗变与实践转向之中。
渠岩:的确如此,在我们这个圈里尤其强调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美学的当代转向应是殊途同归的。在艺术乡建的场域中,我提出要“去艺术化”,有一个关键点在于,视觉主义并不是审美,如果观念正确,实际上我们最终很自然地呈现出来的就是审美价值。
向丽:对,我能理解您这个很微妙的区分,对于乡村的形式主义涂抹抑或乡村美容主义,事实上是视觉主义的强暴,同时隐匿着对于他者的猎奇或偷窥。
渠岩:是的,比如有一些关于乡村的美容术,我是大存质疑和疏离的。乡村百年危机,怎能仅仅用化妆术来解决?!在艺术乡建中,我有自己对于当代艺术的系统性觉知,在没有被完全规训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向丽:在这个意义上,我终于理解了您为何说形式主义美学是思想的末端。正是在与表面的热气腾腾和完全意义上的规训保持疏离的情况下,您在持存一种知识分子的属性,那就是责任与担当。我记得您在《限界的目光》里特别强调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谈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逐渐偏离了自己的逻辑,被商业大潮所裹挟,丧失了最初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立场,又或者沦为浅薄庸俗的政治符号,迎合着某种东方情调。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的跌跌撞撞,变成今天四平八稳的平庸媚俗中,您看到了当代艺术的精神被加以褫夺,当代艺术最为可贵的批判意识沦陷了。王南溟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批判非常犀利,称其为地摊文化,但他对于您的当代艺术之评价非常高。
渠岩:其实我可以通过出售我的作品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从2000年以后,我们这批原来自生自灭的人终于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养活自己,我积压了20年的作品一下子都卖出去了。但在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我想我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正像上海评论家顾真说的,渠岩是在艺术市场最好的时候,选择远离商业喧嚣独自到乡村去了,这是少有人走的路。当然,在做乡建时我是有脉络的,是文化自觉和现实抵抗所为,绝不是一拍脑袋的事。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行为”的是一种语言修辞学的范式。打个比方来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危机就犹如被斩掉头的鸡,头没有了,还跳得很热闹,每天在生产艺术,天天在做展览,但它不知道为什么做,既没有脉络、文本、线索,还缺少批判。其中,没有脉络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这样的阙如也是现实批判的缺席,只流于语言学的游戏。这样的游戏虽然没有太大风险,但往往只是隔靴搔痒。我的《精神在别处》相当于艺术游记,其中我有提到捷克剧作家、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的论点,“在荒诞的现实中寻找和发现积极的意义”,“从自己做起、从良知出发”。这些都对我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哥伦比亚Stinkfish在许村创作的壁画(2015),国际艺术家在许村绘制壁画。渠岩 拍摄

渠岩、向丽对话现场。图片由向丽提供
作者简介:
渠岩,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向丽,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审美人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张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