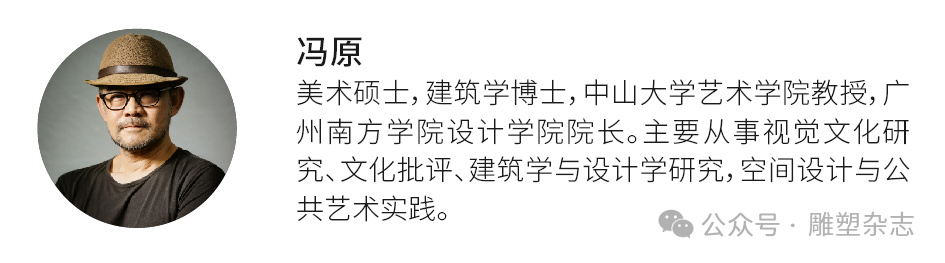访谈 | 冯原:石头与水——寻找感恩之情的永久之形
2024年7月18日,为铭记烽火岁月、赓续文脉精神,中山大学西迁澄江办学纪念苑在云南澄江凤山公园正式落成。该纪念苑由中山大学冯原教授创作设计,通过地域融合象征、核心文化符号、纪事墙叙事三个维度构建历史叙事;采用滇粤两省七种石材拼接,形成七石相融的时空对话;借助历史与艺术的融合,追溯了86年前中大师生在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壮举,也见证了新时代校地合作的深化发展。这不仅是历史记忆载体,更是新时代合作的起点,蕴含了记忆场域与精神坐标双重价值。以下为该纪念苑的设计解读及相关历史资料呈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东北、华北以及华东地区成为主战场,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主要的教育机构全面向中国的西南腹地迁移,这一西迁求存的艰难历程也呈现了中国地理的特征——在东西方向上中国拥有广阔的纵深,多山的西部高原和盆地既是大河的发源地,也提供了阻挡侵略者的天然屏障。
所以,当1938年战事漫延至华南地区,广州沦陷,国立中山大学被迫迁移之时,其迁移的方向也必然是向着西南——这正是珠江水系的流向,沿着珠江最大支流西江一路向西,就是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最后,如同从北京西迁中国西南腹地的西南联大一样,国立中山大学也选择了云南作为安身之处,如此来看,国立中山大学从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广州迁移到珠江的发源地云贵高原,其实是对珠江水系的地理条件的一种适应性选择。

纪念苑主体石墙的侧面
于是,当时隔八十多年,站在中山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2024年,回过头来去纪念和铭刻这一段时隔八十多年的历史——国立中山大学西迁云南、在澄江办学一年半的艰辛岁月,这一时间和地理的叠合,使得珠江之水跃入了我们的思绪之中。想一想,中山大学的西迁虽是战事所迫,但为什么选择西迁云南而不是其它地方?究其根本的原因,仍然是自然地理造成的经济和文化走向,这一切都离不开珠江水系的串连。假如没有珠江,就不会有西迁云南的选择了。
也正因为如此,位于澄江的抚仙湖就显露出了它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性特征。抚仙湖既是澄江的母亲湖,也是珠江的源头之一,更不用说1938年至1940年期间,在澄江的数千名中山大学师生就生活在抚仙湖边上,湖水和澄江人民一道养育了中山大学。于是,抚仙湖——作为湖的形状的自然轮廓,就成为大自然赐予澄江人民和中山大学的一个记忆之形,一个能够唤起情感的符号。如果珠江是一扇门,抚仙湖就是这扇门上的钥匙孔,它的形状浑然天成,让人过目难忘。

主体石墙上镂空的抚仙湖与主体石墙的侧面
那么,我们如何能让抚仙湖的“自然长相”成为永久的纪念,并让它铭刻中山大学的感恩之情呢?从“永久性”这一概念的物质材料属性出发,我们在所有的永久性自然材料中选择了石头,而且选择了石头中最为坚硬和永固的花岗岩,这不仅是因为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古文化都会选择石头营造象征永恒的纪念性建筑,甚至古罗马的维特鲁威说过“石头,就是建筑的史书”这一名言,而且石材的开采和使用也与产地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一石材都会拥有独特的肌理和质感,只能用开采的产地来命名,这就使得石材与产地的人和文化形成某种对应关系,例如,开采于广东的石材(花岗岩)用的是广东地名来命名,这样就形成了诸如阳江红、揭阳红或恩平黑等石材种类,同样道理,开采于云南的花岗石当然也会如此命名,例如云南芝麻灰等。

纪念苑的鸟瞰图
水是无形的,但承载水的湖泊和河流是有形状的(从地图的视野来看);人类的活动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在电影发明之前,并无留存时间的形象载体,但是,透过石头(花岗石)产地的命名关系,使得石头具有了与人和文化的一种联想性关系——产自某地的石头象征某地的人和文化,人类的主体活动就可以透过永久性的石头获得某种表现性的呈现,这样,我们选择了分别产自于粤东西北的六块石头来代表国立中山大学(前身是国立广东大学),这等于用材料来书写这句话——中山大学来自广东(之所以选择六块石头,是因为六块石头形成的石缝会形成一个中字的形状);然后再选择一整块产自于怒江边的芝麻灰石来象征云南和澄江人民,并将它们组成一个最简略的长方形,广东石材位于左边,云南石材位于右边,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并在这个石墙上镌刻出一个抚仙湖的镂空轮廓,于是,在石墙的正面,分别在左边和右边镌刻1938和1940的字样,如此的设计,就让这一个由广东石材和云南石材共同构成的镂空的抚仙湖石墙简洁而完整说出了这句话——云南澄江人民养育了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们,石材表皮的斑驳肌理,述说了八十多年前的艰苦岁月,而光滑细致的抚仙湖轮廓则唤起了感恩之情,让人们想起了澄江人民接纳落难的中山大学师生们的博大胸襟。
这样,以纪念石墙为主体,整个纪念苑由四个部分组成,并分别表达了西迁之痛、办学与养育之恩、告别之情和回顾大事记这四个内容。

主体石墙的后部和“告别澄江民众书”石碑
第一篇章——西迁之痛,用镶嵌于石地板上的黄铜板完整的复刻故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馆长手绘的“西行志痛地图”,人们可以在此低头观看,抚今追昔,缅怀中大师生西迁之艰难;第二篇章,看完地图,即看见三米高的石墙主体,超过人身高的抚仙湖轮廓深入人心,让人心生感动之情;第三篇章,绕过主体石墙,是一块较小的长条形黑色石碑,上面完整镌刻故许崇清校长的“造别澄江民众书”,全文共1110字,由现中山大学谢副校长手书,显现两代中大人对于澄江人民的感恩之心;第四篇章,在离许校长石碑五米外,并排竖立着六块永久性的钢板,上面镌刻由中山大学校史馆整理的二十件大事,并附有五幅铜板刻画的插图,观众们可以在此驻足观看,细细回顾中山大学在澄江一年半的事迹和作为,并为展望中大和澄江的未来提供想象。
也正因为四个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述说了中山大学西迁澄江的历程和事迹,并凝聚成一个感恩的纪念形式,所以,这一组永久性纪念物由中山大学正式命名为“中山大学西迁澄江办学纪念苑”。

纪念苑的正面全景与凤山的轮廓
中山大学西迁澄江办学纪念苑设计项目
项目策划: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创作设计:冯原(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南方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结构与施工设计:胡建强(广州南方学院设计学院教授)
项目管理:辛志亮、李进健(广州南方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广州南方学院设计学院讲师)
图片拍摄:冯原、曾瑜睛、康子馨、盛清泉、刘祎哲、刘一菲、茹帅然(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采访人:杨晓明(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以下简称“杨”)
受访人:徐俊忠(中山大学博物馆馆长,以下简称“徐”)
杨:当年的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西迁办学如何落脚澄江?今天又是如何确定纪念苑的选址的?
徐:当年,中大迁移办学,是在曲折艰难中来到澄江的,学校是在1938年10月20日凌晨开始迁离广州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是21日凌晨,这一天也就是日军入侵广州的时候。学校初迁的目的地、广东境内的罗定,在遭遇包括“汇兑不便”等巨大困难后,又“着即筹备迁往广西”,在迁桂无果后,期望迁往滇省。然而,时任省长的龙云先生回复是:“中山大这迁滇无任欢迎,惟刻间昆明附近各县拥挤异常,无隙可容。”正是在困窘万分的时刻,澄江的人民向中大师生伸出了温暧的臂膀。于是,邹鲁校长1938年12月31日再次致函云南省长:“敬祈即赐指定澄江为敝校地址,以免员生失所。”澄江由此成为中大员工“不致托足无方,尚能安居研读”的福地。

我接受中大领导的指示:带队去澄江,调查当年学校西迁办学旧址状况,并向学校提出以何种形式,留下一个让中大人永志不忘,永远感恩的方案建议。因此之故,我和曹天忠教授、吴重庆教授以及博物馆(校史馆)的同事来到澄江考察。其后,当我为了排除烦琐手续,邀请在公共艺术设计方面很有造诣的冯原教授为项目义务设计和协调创作过程时,他爽气十足地回答:“这是作为中大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人生的荣耀!”
当中大的工作团队触摸着每一处办学旧址时,心里都在颤动:既为先辈们的艰难困苦而颤动,更为澄江民众对从烽火连天的战区颠沛流离而来的中大员生热诚推爱、庇荫有加的义举而热泪盈眶。在澄江市领导的引领下,通过对澄江市内主要公共场所的察看和反复对比,尤其一次奇妙的巧合——与一群在凤山公园里吹拉弹唱市民的聊天中,他们的友善、亲切、乐观、豁达深深地感染了中大的团队,让他们仿佛看到了历史上善良的澄江人民和今天友善的澄江人民是如此的一脉相承。这里也是澄江市民最喜欢的游憩之所,也是澄江市举行重大节庆活动的场所。因此,这就是中大向澄江人民表达感恩之情的最佳场址。实际上从初选到校、市领导现场决定,选址活动至少是经过三次考察才慎重确定下来的。

杨:八十年前的中大员生与澄江民众的守望相助,如今要怎样来加以体现和表达呢?
徐:用“守望相助”来形容当年中大员生与澄江民众的关系,是十分恰当的。查阅当年档案记录和实地察看,以前这里有些路段是不通公路的。当年,当运载中大物质的卡车进入澄江县城时,许多乡亲父老可是第一次看见大卡车都出来围观的!
1939年1月,为便于地方交通,亦因中大物质搬运需求,中大与云南省公路总局在经费和技术上合作,迅速筑成呈贡中关坡至澄江县城公路。通车剪彩当天,搬运中大物质的8辆大卡车,在鞭炮和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开进澄江县城,引得全城父老出门围观。从此,澄江往昆明全程通了公路。
受制于既有条件,中大校本部、研究院、文学院、师范学院以及医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等学院,都只能分布于县城内外各类庙宇,包括文庙、武庙和其他各类庙宇,还有就是祠堂,及新搭简易校舍之中,实验室和稍大型点的仪器设置在呈贡归化村。中大许多学院最终都只能安置在村头村尾的各类庙宇和祠堂里,散落山城各个角落中,条件十分艰苦。因中大员生工警与家属三四千人的到来,衣食住行需求剧增,给澄江当地和民众都带来不小压力和不便。幸好澄江民众的豁达包容,中大西迁在这扎根,员生得以弦歌不辍,游息有所。中大人一块安放“书桌”的净土,使中大人不至于“托足无方”。

纪念苑有一个纪事墙设计——我们遴选了中大迁澄江办学的19件大事,外加“情缘接续谱新章”,一共20件事。希望纽带墙所记载的事,让观众对于八十多年前,中大员生与澄江民众在烽火中守望相助的历史性事件,有更加具象的了解。如今我们把永久纪念物留在那里,是为历史存证留痕,让后人铭记历史,尤其让中大师生饮水思源。这个地方会成为中大学生的研学基地。中大学子将近二十年持续在那里支教,也有不少师生团除在那里开展各种学术工作。中大还发挥医学医疗资源优势,援助当地亲殷墟宾中山医院,希望支持它成成三甲医院的目标,造福当地和周边百姓,还希望它通过进一步的建设,达到具有服务东南亚地区的远景目标。
杨:中大在当年是怎样展开“在地化”科考活动和研究的?
徐:中大人始终铭记中山先生的教诲“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研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坚持学问要不断创造新知,但学问要服务国家、社会的需要,不脱离百姓、不脱离生活,这也许就是中大的学术基因。我们西迁入滇之后,很快融入当地,植根当地,开展各类学术工作,也努力为当地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都是遵循中山先生的教诲。

1939年9月,《中山公论》创刊。该刊以“推进学术活动、增益抗战建国之效能”为宗旨,探讨政治、法律、经济、生产、国防、外交、教育、文化等问题,经及世界名著、科学新知。该刊为日后全校综合性大型学术刊物《中山学报》的前身,更是抗战中的学术火炬。同月,学校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把澄江25个乡镇划分为7个区,由7个学院分别领衔举办,各学院发挥专业优势,分工合作,群策群力,全面施教。在扫除文盲、国民精神运动、实用科技、农业推广、公共卫生以及兴办面向高中毕业生的函授学院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被评价为“本校迁滇期间,对国家对地方之一种贡献”。
开展“在地化”学术考察与研究,是中大的优良学风。中大迁滇后,有感于西南边境土壤情形研究者尚少,特开展当地土壤调查,希望对西南一般土壤情形有所了解,于生产建设上亦有所贡献。1939年10月中旬,农学院土壤调查所和研究院土壤学部共同开展调果研究工作。谢坤、黎旭祥、刘致清等教授组成土壤调查队,对澄江山南盘江沿岸、滇越铁路滴水车站附近的新街、松子园,抚仙湖西岸的路岐、阳宗海畔及草甸乡的土壤进行了调查,历时45天。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多处磷矿,编印成《澄江之土壤》一书,并绘制《云南澄江县土地利用概况图》《云南省县土壤图》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地质系杨遵仪、何春逊在考察澄江帽天山后,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帽天山页岩,从上到下有一种低等生物化石”。这一发现,成为澄江早期海洋古生物化石群发现的先声,启发了后续学者的进一步工作,最终成就了20世纪生命演化重大实践中最惊人的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