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研究 | 孙红杰:数字文化遗产的文明互鉴潜质与文化拾遗功能(一)
现代信息技术持续加剧着人类知识的离心运动和人类记忆的遗忘过程,在此之际,数字文化遗产发挥着整合人类知识、守护人类记忆的重要枢纽作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性和数字载体共同具有普适、关联、承载、耐时四种效应,是不同文化主体实现深层交流和持久互鉴的保障因素。剖析文化遗产的艺术性及其与数字语言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数字文化遗产蕴含的文明互鉴潜质和文化拾遗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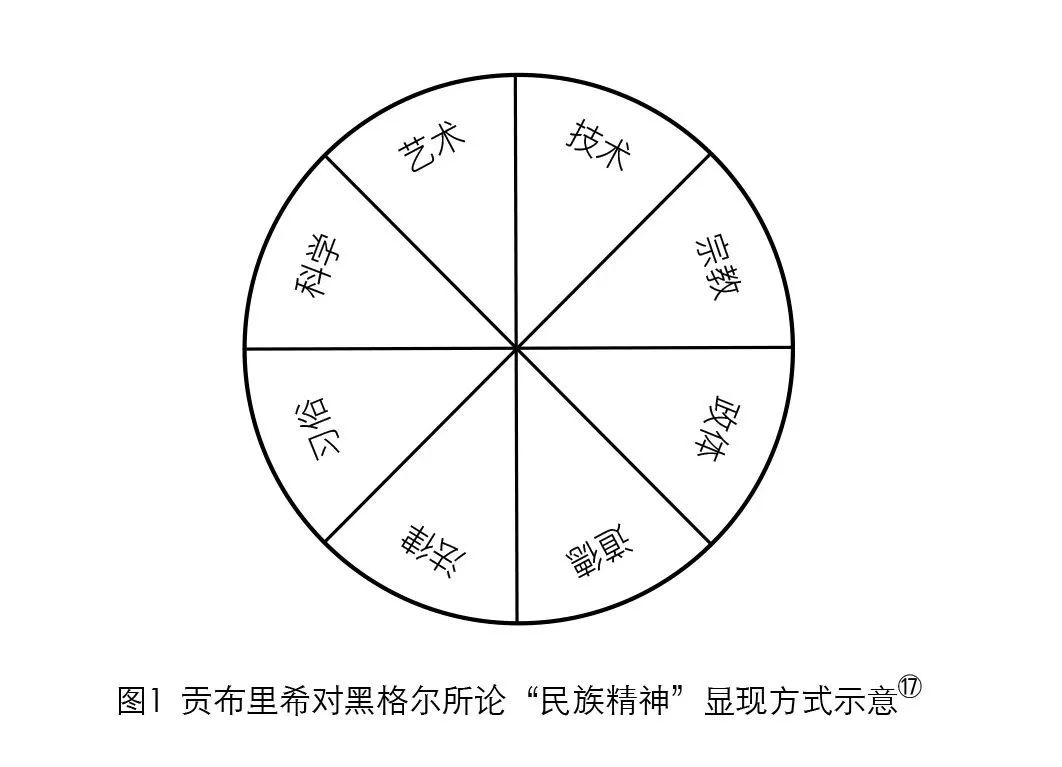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