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 | 魏晋南北朝丝绸文化
纵观魏晋两晋南北朝期间,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分裂、动荡的社会背景,残酷的战争对社会经济和丝绸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在相对安定的时间里,统治者也很注意耕桑。因此,丝绸的生产亦是曲折地发展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势力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加剧了中原政局的动荡的同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
这不仅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蚕桑区域的扩大,而且也使丝绸技术吸取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有技艺而得以提高和发展。

此时期的丝织品规格基本沿用汉朝规格。
北魏时期沿袭旧制,根据出土实物考察,品峪关新城M2出土的木尺长为23.8厘米,当时所有出土的木尺的平均值亦为23.8厘米,可以算得北魏时织品幅宽约为今之宽55.4厘米。
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匹为一端,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
——《魏书•食货志》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一件羊树锦,残存有过半的纬向纹样循环,根据一半的纹样循环来推测,此锦原来的幅宽约为42厘米,比标准的魏制55.4厘米狭一些,这应当是与织物的品种不同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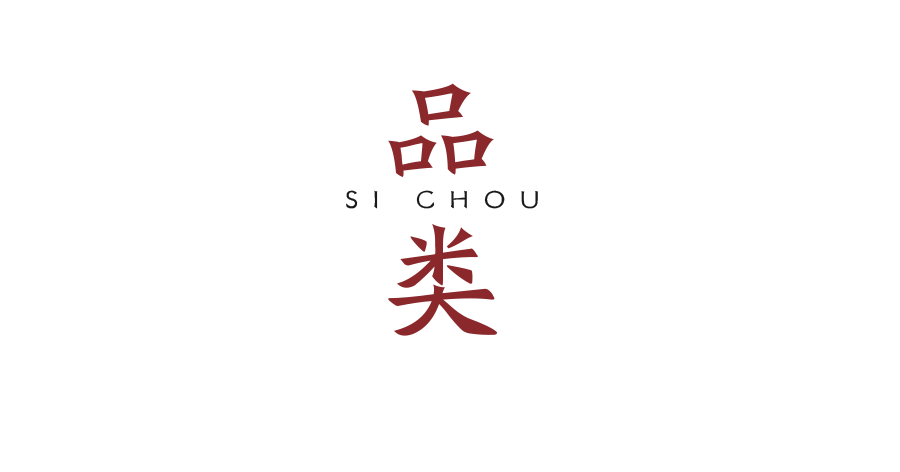 顾野王的《(原本)玉篇》中残存了系部和素部等,其中作为丝织物品名的计有缯、绮、縠、缣、绨、缟、练、䌷、绫、绣、绢、纱、纨、素等20多种。
顾野王的《(原本)玉篇》中残存了系部和素部等,其中作为丝织物品名的计有缯、绮、縠、缣、绨、缟、练、䌷、绫、绣、绢、纱、纨、素等20多种。
单从这些品名,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品种的丰富,在此主要介绍锦、织成两大类。
这一时期的织锦产地主要是以邺城为中心的魏地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因此,当时出现了以地区命名的两类织锦,即魏锦和蜀锦。
魏地的织锦业具有悠久的传统,左思《魏都赋》中有“锦绣襄邑”之称,曹魏时期洛阳生产如意、虎头、连壁锦,此外还有绛地交龙锦和绀地勾文锦。至后赵石虎在邺设置织锦署,生产的锦品类众多。
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记名。
——陆翙(huì)《邺中记》
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其织锦业亦有悠久的历史,蜀锦在三国时已很著名。
织成有两种结构,一种用通经断纬方法织制,另一种是直接编织成成品,在此时期,后一种十分流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吐鲁番出土的“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丝质鞋(图1),鞋上共有红、土黄、肉色、蓝、绿、白、黑和灰蓝八种颜色。其中又分区织出对鸟纹、对兽纹、几何纹、红变形兽纹、蓝地小花纹等不同的花纹,显示了当时织成技术的高度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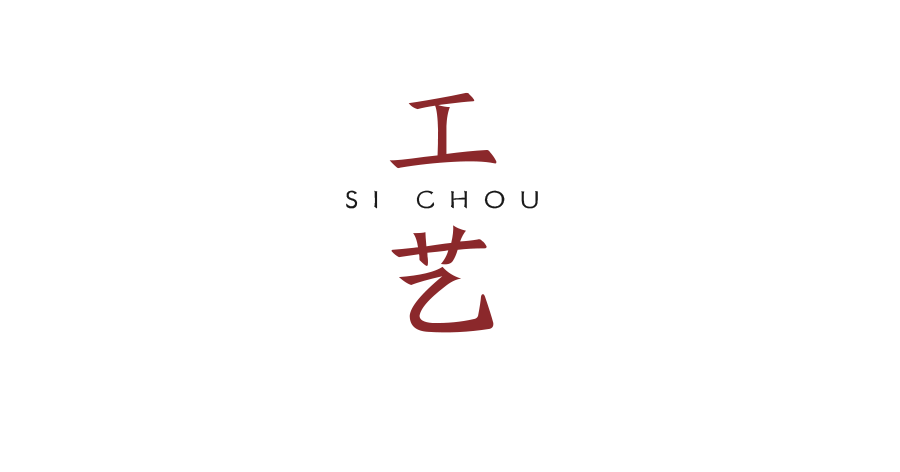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一部在科技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诞生了,作者贾思勰(xié)在书中对蚕桑技术和染色技术作了详尽的描述。
丝绸精练工艺可分为灰练和水练两类。
灰练指的是利用碱性物质使丝脱胶,北朝时仍沿用草木灰精练。水练是依靠水中微生物的水解作用,通过各种蛋白水解酶,对丝胶蛋白起专一的分解作用,从而达到脱胶目的。
水练法虽然需时较长,但在南北朝应用更广。这是因为灰碱性强,难控制,易造成灰伤,因此以水练绸比较稳妥。
染料的使用,与秦汉时差别较大,一些主要色调中的主要染料被一些新的染料所更新。
红色染料中,早期主要使用茜草,在此时期红花染色已大大受到重视,并逐步取代茜草(图2)。

红花摘后一般要经制备,便于贮藏和贩运。制备法在当时称为“杀花法”,《齐民要术》中便记载了杀花法的红花加工技术。
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饭浆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绞去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著瓮器中,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令均,于席上摊而曝干,胜作饼。
——贾思勰《齐民要术》
从文中“胜作饼”一句看,当时制备红花已有“干红花”和“红花饼”两种方法。
以红花入染工艺的特殊性在于红花色素的独特性质。干红花中含有红、黄两种色度,其中红色素即红花素,含量极少(按照现代科学方法测仅0.5%左右);文中黄汁即指红花中所含黄色素,含量在30%左右。这两种色素的性质恰恰相反,红花素能溶于碱性溶液而不溶于酸和水,黄色素能溶于水和酸而不溶于碱。因此,红花的制备、提取和染色等一系列应用技术均是建立在这一原理的基础上的。
—— 华服小百科
我国黄色染料向来很多,在汉时已使用栀子、黄栌、黄檗等。魏晋时仍大量使用地黄染色,主要用于染御黄。
蓝色染料在我国应用极早,汉代以前多为直接染,使用的染料以蓼蓝和菘蓝为主。但在此时,随着木蓝的输入(图3),制靛技术也在中原兴起,从而为蓝色染料的突破时间性和地区性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出土的锦纹样基本作兽纹锦,其中以北凉高昌太守渠封戴墓中所出藏青地禽兽纹锦为最佳(图4)。
其组织为平纹变化经二重,有藏青、缥青、大红、退红、白玉色,而以藏青为地,其他各色分区排列,纹样以不同姿态的祥禽瑞兽为主体,用楼蝶式的云气纹作骨架,进行排列。

纹样在吸取其他民族和外来地区的纹样风格特点,相较之前有了新的突破。
织锦上出现了以圆形骨架为主的纹样,如联珠孔雀锦(图5)。

除了孔雀,纹样题材也出现了象、狮、骆驼等外来动物的形象。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方格兽纹锦用褐、绿、白、黄、蓝色五种丝线制织的平纹经锦。彩条格,中间的纹样作经向重复排列,依次为牛纹、卧狮纹、象纹(图6)。

 丝绸作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
丝绸作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
历代政府均在产丝区的人民身上征取丝绸产品、以供国用和统治阶层的享用。按国家规定征取的纺织品称为调,在此时期主要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征收,称为户调。
当时的产丝区主要还是集中在黄河流域,因此,中原国家一般调以丝绸,而南方六朝均调麻布。
这种制度的存在,以至于后期丝绸的大量生产和汇集官府,这对当时各地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丝绸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尺度两种属性,因此用途之多。在北方,丝绸是当时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的重要俸禄形式之一;当遇到庄稼歉收或天灾,政府常发绢帛等以示救恤;丝绸多寡亦是国家财政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它还可以换取各种所需的物资,三国时蜀国的“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